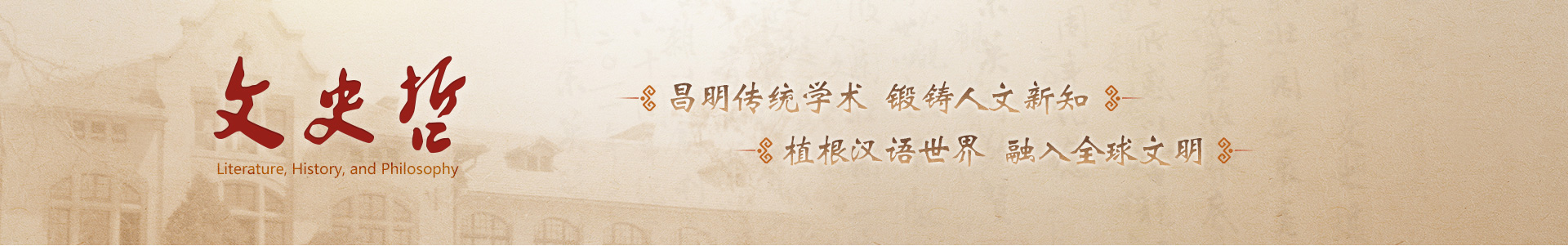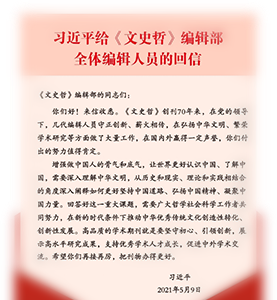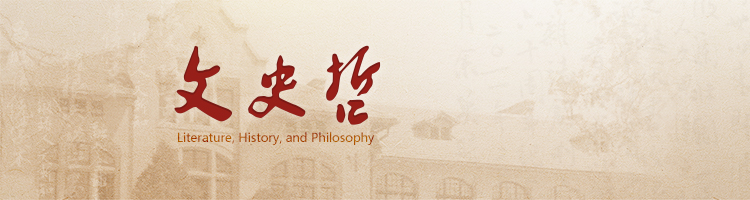|
陈宝箴“赐死”考谬
——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进商榷
李开军
摘要:刘梦溪、邓小军以陈三立诗歌及相关史料“考实”的慈禧“赐死”陈宝箴之说,因其考证过程中的种种讹误,不足凭信。不论是官私文献记载还是陈三立本人的诗文表述,支持的都是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所说的陈宝箴“以微疾卒”。
关键词:陈宝箴 赐死 以微疾卒
关于陈宝箴的死因,在其卒后八十二年始有人提出有别于陈三立“以微疾卒”之新说——1982年宗九奇发表《陈三立传略》一文,首次披露戴远传《文录》中所记陈宝箴被慈禧“赐死”之史料[1]。之后便有人在一般的文史文章中认可“赐死”之说,但学术界反应比较谨慎,鲜有撰文支持者。进入新世纪,这一“赐死”史料几乎同时引起邓小军、刘梦溪二位学术先进的关注,先后发表长文《陈宝箴之死的真相》(以下简称“邓文”)[2]和《慈禧密旨赐死陈宝箴考实》(以下简称“刘文”)[3],以陈三立的诗文作品为基础,以诗证史,周详考证,对“赐死”一事“考实”。至此,陈宝箴“赐死”、陈三立隐忍似已成定谳,并为不少文章所播扬。[4]
但当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5],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崩卒,十月二十五日前后陈三立得讯后[6],为何内心没有丝毫快意,却写下这样一首题为《纪哀答剑丞见寄时将还西山展墓》的诗呢?诗云:
两宫隔夕弃臣民,地变天荒纪戊申。万古奔腾成创局,五洲震动欲归仁。月中犹暖山河影,剑底难为傀儡身。烦念九原孤愤在,忍看宿草碧燐新。[7]
陈三立言两宫之卒为“弃臣民”、“地变天荒”,评价慈禧、光绪领导下行至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的中国为“万古奔腾成创局,五洲震动欲归仁”,这都是相当积极的评价,显然不是听到杀父仇人撒手人寰时应有的反应。因此,有对慈禧“赐死”陈宝箴观点重新检讨之必要。
并且,若细检戴远传《文录》陈宝箴“赐死”之记载和邓文、刘文,就会发现,其中存有不少疑点和有待商榷之处,尤其是邓、刘二文在以诗证史的过程中,颇有牵强和过度阐释之嫌。既然邓文、刘文都是在认同戴远传“赐死”记载基础上进一步以诗证史的,那我们不妨先从对“赐死”记载的分析入手,然后再辨析邓文、刘文的讹谬之处,最后提出我们对于陈宝箴之死的意见。
作者简介:李开军,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济南250100)。
项目简介:本文受“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同时也是作者在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1] 宗九奇:《陈三立传略》,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此“史料”又见于宗九奇:《陈宝箴之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
[2] 邓小军《陈宝箴之死的真相》一文原题《陈宝箴之死考》,为1999年11月27-29日广州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后收入胡守为主编的《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后此文收入氏著《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一书,题目改为《陈宝箴之死的真相》,本文所揭引均据《诗史释证》。2009年8月10日,邓小军在其搜狐博客“邓小军文集”中发表《〈陈宝箴之死考〉书后》,中云:“这些年过去了,回头看此文,除个别之处有误,当作修订外,基本内容并无失误。”
[3] 刘梦溪《慈禧密旨赐死陈宝箴考实》一文刊《中国文化》2001年第17、18期,此前曾以《陈宝箴死因之谜》为题以节略的方式(主要是以陈三立相关诗歌考实陈宝箴“赐死”的部分)刊于《百年潮》2001年第2期,后又以《陈宝箴之死的历史真相》为题,摘要发表于《中国艺术报》第405期(2003年5月16日)。该文获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刘梦溪后来又在《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7月27日)等文章中重提慈禧赐死陈宝箴的观点。
[4] 请参阅郑海麟:《从黄遵宪〈与陈伯严书〉看晚清变局》,《文史知识》2009年第10期;郑海麟:《陈宝箴、黄遵宪交谊与湖南新政》,《文史知识》2008年6-9期;陶江:《崝庐与陈宝箴之死》,《创作评谭》2007年第3期;马英典:《陈宝箴与近代警察制度》,《兰台世界》2006年第23期;陈柏生:《揭开九十年前的一桩历史疑案》,《湖湘论坛》1992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对“赐死”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如张求会在其《陈寅恪的家族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胡迎建在其《一代宗师陈三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中,都以为宗九奇所提供的“赐死”记载为孤证,不可遽信,胡氏并拣刘梦溪文中数处错误予以辨正。
[5] 本文正文及注释中的日期,阴历以汉字表示,阳历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6]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云:“得太皇太后凶问,异哉。”时缪荃孙、陈三立同居南京,且交游甚密,则可知陈三立亦当于是日前后得此讯。
[7] 陈三立:《纪哀答剑丞见寄时将还西山展墓》,《散原精舍诗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0页。
……
《文史哲》2011年第一期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