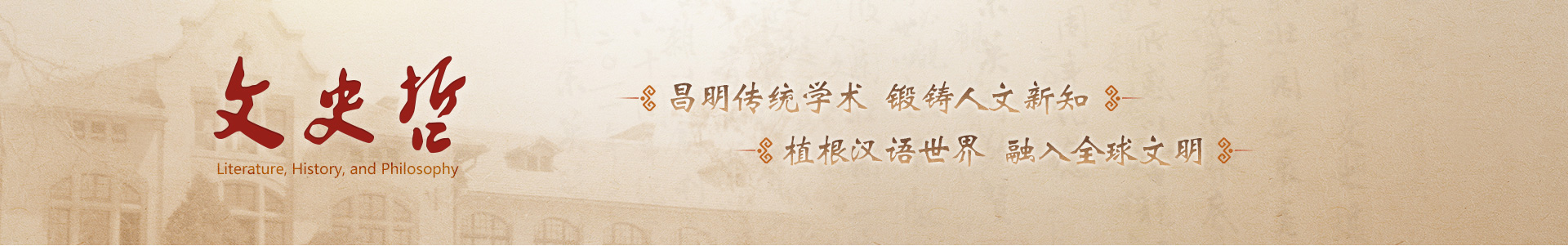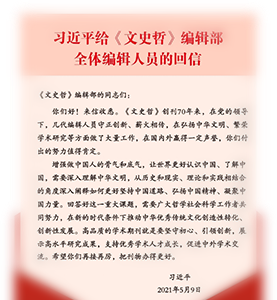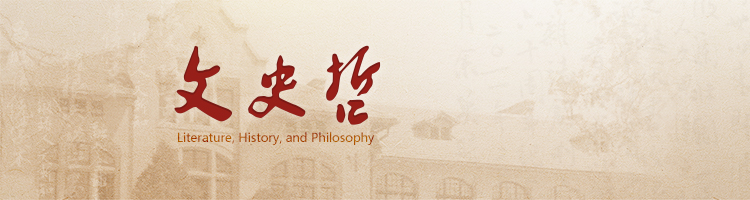各位学界学辈、各位期刊界前辈,各位领导、各位学界同仁、各位来宾:
今天,对《文史哲》编辑部而言,是一个盛大节日,这么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和处在学术第一线上的少壮派学者的杰出代表,这么多编辑部的旧友新知,前来庆祝《文史哲》的60华诞,《文史哲》编辑部的每个成员都感到格外兴奋、激动和荣幸!大家的出席,是对《文史哲》的最高奖赏,可以说胜过《文史哲》所获得的所有大奖!在此,我代表编辑部所有成员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史哲》杂志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60年的不平凡历程,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和学术上的风风雨雨,在这一过程中,《文史哲》杂志自身也成为许多重大学术事件的发源地。因此,《文史哲》杂志既是当代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见证人,又是这一段波澜壮阔学术史的重要创造者。正是在这种剧中人和剧作者双重角色的互动中,《文史哲》逐步从一个同人杂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中国政府出版奖期刊奖的最高领奖台。毫无疑问,《文史哲》为60年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与此同时,它也收获了与它的贡献完全相称的那份荣誉,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和好评。饮水思源,在庆祝自己60岁生日的时候,在《文史哲》收获自己荣誉的时候,《文史哲》首先感谢60年来她的所有作者,正是前后数代作者为《文史哲》赢得了今天,编辑部首先感谢您们!感谢您们60年来的厚爱,感谢您们所提供的一篇又一篇呕心沥血之作!《文史哲》所有的荣誉之花,可以说全都是由您们的心血所浇灌!《文史哲》编辑部还要在此感谢广大读者,特别是感谢为我们提供各种各样帮助、支持、关照的各界朋友和领导们!正是由于您们的呵护和偏爱,《文史哲》才能走到今天,您们是《文史哲》一刻也不能缺少的动力,没有您们的特殊关心,《文史哲》办不下去,尤其是不能办好!《文史哲》60年的历史,当然离不开作者、读者和各界朋友,同时更离不开那些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甘为人作嫁衣裳的编者。《文史哲》这些编辑同仁的名字可能进入不了学术史,也可能不为人们所熟知,但他/她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文史哲》的功臣,都将永远进入《文史哲》杂志的先贤祠中!作为一份远离学术中心,办在地方上的杂志,《文史哲》每走一步都不容易,需要感谢的人太多,需要感谢的方面太多,这些方面和这些人虽不能在此一一列举,但《文史哲》永远不会忘恩负义,永远会记住为她的成长提供过各种形式帮助与支持的所有领导、朋友和同道!我曾代表编辑部在许多场合说过一句话,《文史哲》永远是所有外地学者和朋友的驻济办事处、接待站和联络点!
一个进入花甲之年的人对人生一定有了许多体会,一份进入花甲之年的杂志也一定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在这个隆重的场合,我代表编辑部把我们对如何办刊的一些认识和一些并不见得有什么价值的做法在此作个简要的汇报,目的是希望得到各位的指点、批评和建议。
坚定不移地走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是我们最重要的办刊体会。文、史、哲三个学科特别是文、史两个学科,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国的国粹所在,是中国所有其他学问的母体,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和积累,因而是现代学林中最厚重的学问,这决定了主要刊载这方面成果的《文史哲》杂志除了走厚重之路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文史哲》所刊出的大都是专家和学者们的积年之作,学术含量的高低和学术功力的深浅一直是编辑部取舍稿件的基本尺度,在这方面,《文史哲》杂志的最高追求,是希望它所刊布的作品,能更多地进入未来的学术史之中。60年来一直如此,近十几年来尤其如此!所以,《文史哲》决不会跟风,也决不能跟风!《文史哲》必须有自己的主见。《文史哲》既要引领学术潮流,又不能追风猎奇,走轻浅轻浮之路,不能搞那些短、平、快的东西,不走哗众取宠的捷径。刊发在《文史哲》上的文章当然希望能被更多文摘刊物转载、摘要和传播,但《文史哲》决不能被转载率所左右,甚至被转载率牵着鼻子走,我们办刊物的目标实际上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学术”本身。对《文史哲》而言,“学术”之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不能不要,但决不应成为我们的追求所在!
强调“学术”,强调厚重,决不意味着要把《文史哲》办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办成老古董,相反,从创刊伊始,《文史哲》就具有非常浓厚的入世情结,就具有干预学术走向的强烈愿望,而且在若干时期《文史哲》也部分地把这种愿望变成了现实。因此,《文史哲》的另一个传统,就是力图站在学术前沿,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下的学术界,自觉充当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在我看来,《文史哲》是沿着下面三条主要路径走入波澜壮阔的当代学术史的。第一,是下大力气推动、倡导、实践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方针。《文史哲》60年来所享有的盛誉,可以说主要得自于它所发起和推动的一场又一场学术论战和重大讨论。著名的“《红楼梦》问题讨论”仅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由于这一点人所共知,故不在此多说。《文史哲》参与创造当代学术史的第二条路径,是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我们认识到,一个杂志的影响力取决于该杂志锻造公共学术话题的能力,你提出的话题越多、覆盖面越广,敏感度越高,影响力可能就越大。这里的敏感度不是指政治上打擦边球,在意识形态上搞花样,这里主要是指你能不能、你敢不敢触及学术史上比较重大甚至成为风气、成为主流、成为倾向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敢不敢在学术上反成为潮流、成为主流、成为风气和倾向的观点和主张?这对许多杂志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文史哲》在这里已经找到了巨大的空间。第三条路径,编辑部就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主办相关会议。主办相关会议意味着编辑部在主流问题上,应该拥有若干话语权,应该在关键学术领域发言,至少应积极介入到一系列重大问题讨论中去,从而实现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初衷。学术会议向由学术社团来发起或主办,由杂志社来举办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并不多见。从2008年起至今天下午,我们已连续四年举办以“人文高端论坛”为名的系列学术会议,论坛之一是“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论坛之二是“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论坛之三是“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论坛之四,就是今天下午即将举办的“反省与展望: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加上2006年举办的“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暨上古史重建学术研讨会”,我们共主办了五次高端学术研讨会,这五次会议全部围绕一个主题:如何言说和诠释文化中国?最终要回答的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未来走向。
坚持百家争鸣、锻造学术话题、主办学术研讨会,在做上述一切时,我相信历代《文史哲》人肯定都基于一个理念:在学术发展的历程中,并非只有作者、学者是主动的,在推动学术发展上,学者与期刊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从而使期刊在学术史上扮演一个比以往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的角色,我认为,做到了这一点,学术期刊才算尽到了自己应尽的学术职责!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民国年间的《禹贡》和《食货》杂志给所有的期刊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榜样。
《文史哲》还有一种探索值得在这里汇报,这就是我们在打通学科壁垒方面所作的努力。综合性大学学报如何办?已经成为期刊界议论纷纷的问题。目前人们看到的只是综合性的劣势和不足,但如何把综合性的劣势变成优势,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与学科越分越细的趋势相反,我们感觉一个综合的时代即将到来,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本身已越来越带有综合的性质。在这一背景下,《文史哲》杂志绝不应该成为中文、历史、哲学三大学科文章的外在组合。众所周知,《文史哲》所主要刊发的是古文、古史、古哲方面的文章,亦即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而中国古典学术在过去是一个整体,在古典学术上实际上很难分科治学,如“儒学”等等就是如此。即使不是古典学术,我们也在努力约发那种亦文亦史亦哲、非文非史非哲之作。那么,什么才是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呢?这就是必须提出一些超越学科壁垒的“问题”或“话题”,也就是说,把“问题”看得比学科更重要,更带根本性。《文史哲》应以“问题”为中心,不应以学科为中心,要以“问题”为中心来整合学科,而不应以“学科”为平台来切割“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重点刊发那些《文学评论》、《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等杂志不好发、不便发、感到比较棘手、学科归属感不强的稿子。譬如,我们所提出的“疑古与释古”这个话题,就是任何专业杂志都不便面对的问题,因为它不但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大的学科,更包括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完全不同的方向和领域,这样的问题放在《文史哲》上来讨论就再合适不过。总之,我们要力求在单个课题和选题上能体现出综合性和跨学科来。像“人文前沿”、“当代学术纵横”、“海外汉学”和本期新开辟的“历史与伦理”等栏目,就都能体现出我们的这种努力和追求。
《文史哲》杂志还有一条广受称道和赞誉的做法,这就是她对所谓“小人物”的发现和不遗余力的扶植。从《文史哲》杂志出发走向学坛的专家可以说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座的李希凡先生、庞朴先生,以及李泽厚先生、汝信先生、汤志钧先生等等。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在座的李振宏先生,他也是在大学二年级就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文章,并且一举成名。我们认为,一份杂志的不朽和成功,不仅在于她能吸引多少名家,更在于她能发现、扶植和造就多少名家。杂志造就名家,名家成就名刊,《文史哲》在其中付出了自己的胆识和辛勤的汗水,这些从《文史哲》出发的学者后来也用自己所获得的成就给《文史哲》带来了巨大声誉。《文史哲》有理由为自己在发现和造就杰出学者方面的辉煌贡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发扬和光大《文史哲》的这一传统,更多地关注和关心“小人物”,腾出更多的版面给那些青年才俊,仍是《文史哲》的今后主要努力方向之一。
一贯走专家办刊之路,力争把一流专家引入到编辑队伍中来,是《文史哲》杂志的又一传统,创刊时期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为何只有专家才能办刊?1. 只有专家才有应有的鉴别力和判断力。一直以来,对杂志威胁最大的不是抄袭、不是剽窃,而是低水平重复。也就是说,没有知识增长意义的论文占了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如何沙里淘金,怎样百里挑一,这就必须要求编辑要有相应的眼力、判断力和洞察力,严格说来,只有专家才具备上述这些能力。2. 只有专家才有选题策划能力。《文史哲》要求所有的编辑必须具备选题策划能力,消极地被动地充当一个技术编辑是不称职和不合格的。我个人的一个深刻体会是:办杂志必须策划,必须主动出击,绝不能守株待兔、等货上门,这一点关乎《文史哲》这样一份办在地方上的杂志的生死。目前所有学术杂志面临的一个共同困境是:优质学术资源日益稀缺与有限,而参与瓜分这一有限资源的杂志则越来越多,这形成一个尖锐矛盾。在这一困境中,谁缺乏策划选题意识和坐等来稿,谁就必败无疑!3. 只有专家才知道如何处理稿子。因为只有同时懂得研究甘苦和写作甘苦的人才知道如何编辑稿件才能既让作者满意又同时符合规范。因此,编辑部要求编辑要增加对每一篇文章的编辑含量,责编必须动手,尤其是必须动脑,乃至提出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章刊出之后,表述上如还有不通之处,论述上如还有漏洞,那就是编辑部的责任,严格地讲已和作者无关。强调上面这些,目的是告诉专家学者们,您们的大作力作,在《文史哲》一定会受到、一定能受到最郑重的对待,《文史哲》编辑部是大家的学术知音!
《文史哲》的历史是辉煌的,《文史哲》的未来则有待于我们来创造。《文史哲》下一步努力的总方向是为创造“百年名刊”或“世纪名刊”而奋斗。现代学术期刊出现于20世纪初,但1949年所发生的沧桑巨变把百年历史全部斩为两截,20世纪的期刊史也被斩为两截,20世纪前半期的期刊没有一份延续下来,新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是《新建设》,但《新建设》自1966年停刊后再没有复刊,继《新建设》而起的综合性杂志,就是《文史哲》,《文史哲》由此成为迄今为止新中国历史最长的期刊,所以,《文史哲》承荷着率先成为“百年名刊”或“世纪名刊”的历史重任,要考虑的是不止十年的未来,是更长远一些的未来。《文史哲》下一步的具体工作与这一总的把握有关。
根据学校部署,特别是根据徐显明校长的意见,下一步《文史哲》的首要工作是加快自己走向世界的步伐,积极介入世界汉学界的活动,力争成为世界汉学学术圈的一个更重要的成员。与此同时,《文史哲》还要尽快推出自己的英文版,前期的调研工作已经完成,英文版编辑部的组建工作也正在进行,我们争取在2011年底推出《文史哲》英文版的创刊号。根据海内外朋友们的一致建议,未来的《文史哲》英文版是专题性的,每期推出一个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