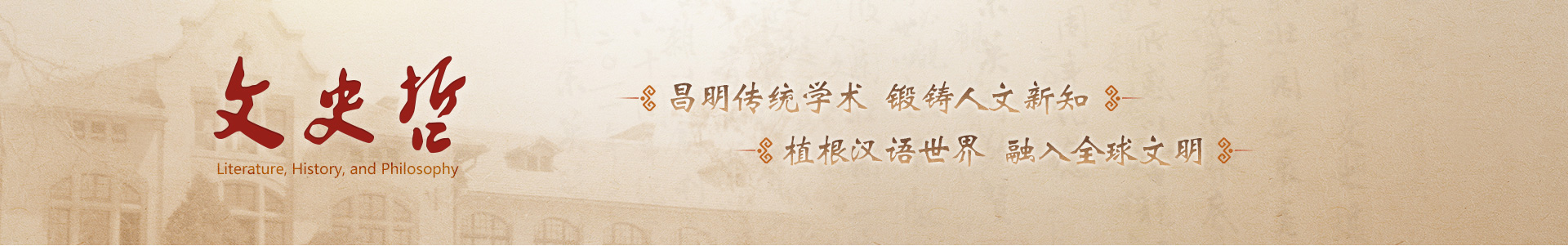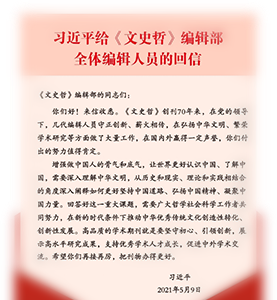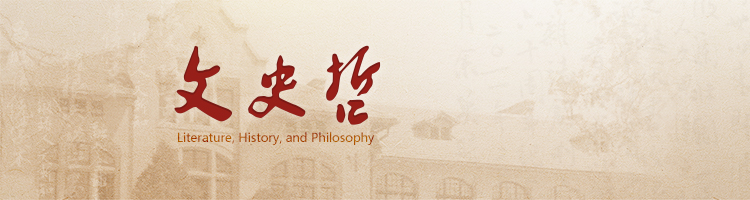“《文史哲》杂志自创办以来,掀起过一系列大论战。允许不同学术意见在同一份杂志上共同向读者陈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是《文史哲》杂志一直坚持的一个方针。我希望每一期《文史哲》都飞沙走石,尘土飞扬,人仰马翻。”现任《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先生在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晚会上如是说。的确,在当今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杂志像《文史哲》这样对学术争论情有独钟。翻检已创刊60年的《文史哲》,再与新中国的学术史进行对照,就会发现,策动当代学术史上那些影响巨大的争论的风暴眼,许多都会定位在《文史哲》杂志上。在《文史哲》杂志上打起的浪头,是推动当代中国学术之河向前奔流的重要力量。“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在《文史哲》杂志上屡屡再现的学术风景。所以,余英时先生才会在《文史哲》创刊60周年时如此写道:“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文史哲》杂志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
“知出乎争”,学术贵在争论,真理愈辩愈明。没有争论的学术难避冬烘。学术史上隆起的崇山峻岭,多是由不同板块学者之间的角力拱起。人类文明往往要依托一场场战争来除旧布新,学术的发展也要凭藉一场场学术论战来别看生面。在《文史哲》60年的出刊史上,大大小小的争论无计其数,如果将这些争论串起来,恰似一条绵延的岛链,可以清晰勾勒出新中国学术发展的海岸线。无论从密度还是规模来看,《文史哲》杂志都堪称新中国学术争论的主战场之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文史哲》推动论战的情结似乎与生俱来。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7月1日出版的第2期便先声夺人,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中国古史分期大论战。在这一期杂志上,山大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发表了《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由于古史分期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更关系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所以该文一经发表,即如巨石击水,立刻激起狂波巨澜。史学界的头面人物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白寿彝、尚钺、日知(林志纯)、何兹全、李亚农、唐兰、金景芳、周谷城等著名学者纷纷参战,彼此展开激烈辩论。在这场几乎动员整个历史学界力量的大论战中,来自山东大学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童书业、王仲荦等几位著名教授皆是风云人物,他们形成了这场讨论中实力最为整齐雄厚、贡献最为卓越的方面军,而他们的主要阵地便是《文史哲》。《文史哲》杂志堪称这场大论战的旗帜,无论是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还是魏晋封建说,都能在《文史哲》上找到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古史分期讨论是《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学术大讨论,正是凭借此次讨论,新生的《文史哲》甫一亮相便博得满堂彩。
可以说,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是在一次次论战高潮中度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的主体便是所谓的“五朵金花”,而其中的三朵(古史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的。仅此一端,《文史哲》就足以笑傲天下。一份杂志的历史能够和一个国家的学术史高度重合,这是这份杂志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誉。
在《文史哲》所发动的诸多学术争论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推“红楼梦研究”大讨论。1954年,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者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对“红学”权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了尖锐批判。这篇文章因为最高领袖的介入,在全国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红楼梦研究”成为当时整个文化学术界的中心话题。虽然这场学术争论后来逐渐演化成对胡适的政治批判,但仍然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杂志的发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开端,使《红楼梦》研究继20世纪20年代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建立“新红学”之后,实现了“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敢于向权威的、主流的、占压倒地位的观点进行挑战,一直是《文史哲》秉守的品格。主持公道,给学术界不同声音、持相反意见的人提供版面,更是《文史哲》由来已久的传统。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质疑和批评上。作为少有的“国家级”的学术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地位在人文社科领域罕有其匹。由于它的官方属性,且大腕云集,其权威性似乎不可质疑。人们被这一工程的超豪华的阵容和多兵种大军团作战的作业方式所震慑。它所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并广泛波及到历史、哲学、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众多领域,大有一统江山之势。这种浩浩荡荡的气势,完全掩盖了这一工程存在的重大偏颇和缺陷。
“夏商周断代工程”初步成果公布后,遭到海外学术界的尖锐批评和质疑。国内虽有不同意见,但迫于某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声音相当微弱,且多藏匿在网络媒体,甚少见诸报刊。面对这一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文史哲》挺身而出,从2006年3月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20多篇重头文章,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起了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引起了整个文化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中华读书报》有文章评论说:“主流学术期刊针对某一学术话题,展开如此大规模的、系统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近年来在学术界实在罕见。而针对近年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走出疑古时代’提出如此篇幅的、系统的正面批评,可以说是首次。”也有学者将“‘走出疑古时代’遭受质疑”列为2006年人文学术界六个重大事件之一。这场引人注目的学术争论澄清了当前古史研究中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并试图对古典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方向性失误进行反思和纠正。这是学界给予这场讨论高度评价的原因之所在。
一段时期以来,“空心化”“碎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生态。由于缺乏对重大学术问题的提炼和抟构,学界似乎正在陷入失重状态。这种状态用“有面积无体积”来形容也不为过。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关系到中国学术未来发展的质量。面对这一问题,《文史哲》再一次表现出它不同流俗的眼光和境界。在《文史哲》编辑部看来,学术期刊应当积极介入学术界,应该在学术史上扮演一个比以往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应通过提出和创造重大学术话题,更多地发挥对学术潮流的“引领”作用。从2008年起,《文史哲》杂志每年举办一次“人文高端论坛”,邀请国内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就杂志社提出的人文学术的焦点、前沿问题进行讨论,陈来、汪晖、秦晖、张汝伦、冯天瑜、萧功秦等著名学者都是论坛的座上客。这种将学术界顶尖高手集中起来,以华山论剑的方式讨论重大学术问题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论坛有关“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被《光明日报》与《学术月刊》两家权威机构列入“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海外一些媒体如日本著名汉学刊物《东方》等也对论坛的情况作过详细报道。通过召开系列论坛,《文史哲》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发表平台,它更担当起学术研究的组织者、引领者的角色。目前具有这种引领学术发展的自觉和魄力的期刊并不多见。在引领学术潮流这方面,《文史哲》似乎在直追民国名刊《禹贡》和《食货》的风范。
回顾发生在《文史哲》杂志上的这些学术争论,就好像是在欣赏一朵朵绽放在学术史上的思维之花。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曾经说过:“就像伟大的斗士总是瞄准敌人的咽喉要害一样,伟大的科学家总是探索可能有重大发现的突破口。”60年来,《文史哲》通过一系列关键问题的讨论,不断推动着人文社科研究的突破性进步,从而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画面。作为一家老牌的人文社科杂志,在当今学术大发展的时代,相信《文史哲》会通过开展更多的学术争论,在繁荣学术的道路上砥砺掘进。